如果你在焦虑 AI 导致的大规模失业, 那不妨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
在 2025 年,有多少人的工作完全用不到电脑和手机?
如果你给出的答案是非常少,那你可以一边看文章,一边再想想,我们会在文章的中部计算这个数字与百分比。
过去两年,关于 AI 的焦虑几乎是“超级传染病”。我们焦虑自己,一个做了十年 PPT 和 Excel 的“白领”,会不会在三年内被一个更懂提示词的毕业生,甚至一个 Agent 所取代。我们也焦虑孩子,现在让他去学画画、学编程、学金融,等到他 20 年后大学毕业,这些行业是否还存在?
这种焦虑并非毫无来由——不管 AI 最终导致的结局是全民福祉还是后乌托邦,但几乎所有的权威机构都在渲染它的短期阵痛。
比如,世界经济论坛(WEF)在它最新的《2025 年未来就业报告》里,用各种图表轰炸我们,核心思想就是“结构性变革”和“技能更迭”。普华永道(PwC)的《2025 年全球 AI 就业晴雨表》说得更直白,在那些“更易受 AI 影响”的行业里,每个员工的收入增长是其他行业的三倍,技能变化的速度快了 66%。
就连 AI 的“始作俑者”OpenAI 也不忘出来“火上浇油”。他们在《智能时代的工作》报告里,兴高采烈地分享了沃尔玛如何用大模型处理商品数据,声称“如果没有生成式 AI,(同样的工作)需要近 100 倍的现有人手才能在相同时间内完成”。
翻译过来就是:技术很棒,变革已至,你不学习,就请出局。
这套逻辑是如此的严丝合缝、不容置疑,以至于“终身学习”和“拥抱 AI”成了这个时代唯一的“政治正确”。
但是……
万事皆有“但是”。
这个“但是”就是:我们默认了一个前提——AI 是一种更高级的“智能”,它将取代人类的“智能”。可现实是,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工作,压根就不需要那种“智能”,甚至连人类现有的“智能”都不需要。
或者说,它们不需要“思维智能”。它们需要的是“物理智能”。
一个软件工程师,他的全部工作都在数字世界里完成。AI 作为一种更高效的数字处理工具,当然可以辅助他、增强他,乃至取代他。
但一个建筑工人呢?他的工作是搬运、砌筑、捆扎,他需要学习的是腰部如何发力避免损伤。一个在后厨切菜的帮厨,一个在小区里巡逻的保安,一个在田里插秧的农民,一个在产线上拧螺丝的工人,一个打扫办公室的保洁阿姨……这些工作的共同特征是,他们仍以物理世界的“原子”为主要操作对象。
他们当然也会用智能手机刷短视频、和家人微信聊天。但在他们的核心工作流程中,他们需要的是一双手,一双腿,和物理世界的在场。除非“人形机器人”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善且降价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,否则对他们的工作几乎毫无影响。
而将 AI 的“数字智能”灌注到“物理原子”里,成本是极其高昂的。我们谈论 AI 替代程序员是“Yes/No”的问题,谈论 AI 替代保安,则是一个“ROI”(投资回报率)的问题。在后者这个领域,人类的物理成本,低得惊人。
那么,这个“但是”所代表的群体,到底有多大?
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,我让 AI 跑了两份估算报告。一份关于中国,一份关于全球。我刻意让它们不要去引用那些“AI 将影响 X% 工作”的宏大报告,而是要求它们基于最基础的全球劳动力结构数据(例如国际劳工组织 ILO 和各国统计局的数据),去估算一个“下限”:
到底有多少人的工作,在核心流程上,是“非数字依赖型”的(完全不依赖手机和计算机)?
结果令人咋舌,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情况:
这份报告用了两种口径交叉验证,基准数据是 2023 年中国的 7.4 亿就业人口。
第一种是“自上而下”的反推法。它依据的是官方发布的《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(2024)》。报告显示,全国就业人员中,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占 67.85%。
反过来推,就有 32.15% 的就业人员(约 2.38 亿人)不具备初级数字素养。
请注意,这只是一个“下限”。它估算的是“因技能缺失而无法参与数字工作”的人。但现实中,还有很多人(比如小区保安)“具备”素养(会用 Excel),但“岗位”不需要。
所以,第二种“自下而上”的估算更接近真相。它不关心人“会”什么,只关心“岗位”需要什么。
它把三次产业分开来看:
- 第一产业(农业):约有 1.63 亿就业人员。这份估算报告假设,其中至少 85% 的工作(如种植、养殖的田间劳动)是纯粹的物理劳动。这部分是 1.38 亿人。他们可能会用手机看天气或卖货,但“种地”本身是非数字的。
- 第二产业(工业与建筑业):约 2.12 亿就业人员。这需要排除那些高度自动化的“智造”工厂和管理岗。估算主要抓取了“建筑业”和“低端制造业”及“采矿业”等体力劳动者。估算这部分总计约 1.06 亿人。他们是工地上搬砖的工人,是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装配工。
- 第三产业(服务业):这是最复杂的部分,总计约 3.58 亿人。这里面既有高度数字化的金融、IT、科研(约 1 亿人),也有中间地带(如教师、医生、司机),还有纯粹物理劳动者。这份估算保守地提取了那些“在场服务”的体力劳动者,如家政、保洁、安保、以及餐饮后厨等。估算这部分约 0.5 亿人。
把这三部分加起来:1.38 亿(农业) + 1.06 亿(工建) + 0.5 亿(服务业) = 2.94 亿人。
结论是:在中国,每 10 个劳动者中,约有 4 个人(32.15% 至 39%)从事的工作,其核心流程完全不需要计算机、平板或智能手机的操作。
这甚至不包括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,这种虽然不怎么需要操作,但与网络强相关的新型就业岗位。
黄框部分由 AI 经真实统计数据以特定计算方式估算而成,在 Gemini 与 ChatGPT 不同产品的 Deepresearch 模式下使用相同 Prompt 多次重复计算, 比例自 35%-45% 之间浮动,但不小于 35%。
这个数字,是否已经颠覆了你对“数字化中国”的认知?
别急,中国的劳动数字化程度,其实已经算很高了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情况。
全球的计算使用了相同的“自下而上”的劳动部门分解法,主要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,以 37 亿总劳动人口作为就算的分母。
它将全球的“物理劳动力”分成了三大块:
- 农业工人:在全球范围内,这依然是最大的“物理劳动”群体。估算约 8.29 亿人。他们构成了全球“物理劳动力”的 38%。
- 非正规服务业工人:这是全球经济的“底色”。包括家政工人、街头摊贩、小商小贩、手工匠人等。他们是全球贫困人口的主体,其工作高度依赖体力。估算约 7.66 亿人(占 35%)。
- 工业体力劳动者及正规服务业中的体力劳动者:包括建筑工人、非数字化工厂的工人,以及正规服务业中的清洁、安保等岗位。估算约 5.73 亿人(占 27%)。
三者相加:8.29 + 7.66 + 5.73 = 21.68 亿人。
结论是:截至 2025 年,全球约有 58.6% 的劳动者,在工作中完全不需要计算机操作。
黄框部分由 AI 经真实统计数据以特定计算方式估算而成,在 Gemini 与 ChatGPT 不同产品的 Deepresearch 模式下使用相同 Prompt 多次重复计算,比例自 45%-60% 之间浮动,但不小于 45%。
至少一半。
这意味着,个人电脑革命(始于 1980 年代)、互联网革命(始于 1990 年代)和移动互联网革命(始于 2010 年代),这三波巨浪,过去了近半个世纪,甚至都没能将全球一半的工作“数字化”。
我们,这些每天在屏幕前工作 10 小时、焦虑着 AI 动态的人,只是不到一半的“数字劳动力”。我们误以为自己代表了全世界,但实际上,我们甚至不是大多数。
现在,我们可以回头再看 AI 的冲击了。
当然,说 AI 对这近 50% 的“物理劳动力”毫无影响,也是不准确的。比如对运输业的司机而言, 网约车这种形态的出现,曾在几年前让传统出租车司机感到了空前的危机。但网约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在劳动技能上没有明显的晋升,它对出租车司机这一岗位更像是一种平移而非替代关系。
甚至可以说,移动互联网从无到有地催生了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员这三个庞大的“就业保障网”。
AI 时代大概率也是如此。AI 会重整数字世界的工作流,创造和挖掘出以前不存在的新需求(比如,AI 生成了 1000 种个性化商品方案),但 AI 自身无法覆盖实现这些新需求所需的所有“物理环节”(比如,谁来完成这 1000 种个性化商品的打样、打包和配送?)。
这些因为 AI 提效而产生的、AI 自身又无法覆盖的“物理缝隙”,恰恰就是 AI 创造新岗位的来源之一。但即便如此,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依然出现了:
一个在过去 30 年里,没有赶上计算机浪潮、没有赶上互联网浪潮、甚至在智能手机时代也只是把手机当作娱乐工具的“非数字依赖型”劳动者……
他,反而在这波 AI 浪潮中,处在了最安全的位置。
AI 冲击的,恰恰是那些在上一波浪潮中“赢了”的人——那些依赖“数字智能”工作的人。
那个在格子间里分析数据的金融分析师,比那个在工地上和泥的建筑工人,更危险。 那个在电脑前 P 图的美术设计师,比那个在后厨切墩的帮厨,更危险。 那个敲击键盘的程序员,比那个打扫办公室的保洁阿姨,更危险。
因为 AI 替代“数字工作”的成本(算力、电力)正在飞速下降,而替代“物理工作”的成本(机器人硬件、维护)却依然高昂。
而这,恰恰揭示了“AI 焦虑”的本质——它在根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焦虑,一种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现代版本。
为什么这么说?
那些“物理”工作,那些全球近一半的人赖以维生的工作,它们通常意味着什么?我们心知肚明:更低的收入、更差的环境、更重的体力消耗。
全球 21 亿人,又或者说中国的 3 亿人,他们一直都活在这种叙事所描述的“危险”之中。不是被 AI 替代的危险,而是被贫穷、工伤、酷暑、严寒和物理消耗所困的危险。
但在“AI 革命”的宏大叙事中,这一半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。他们的“危险”被视为了背景板,被视为了不可接受的结局。
现在,当 AI 出现时,那 40% 的“数字劳动力”(或者说,我们)开始焦虑了。我们在焦虑什么?我们焦虑自己会“失去工作”。
但我们真正恐惧的,是我们会“下沉”——我们害怕自己不得不离开舒适的空调房,去从事那些我们曾经“忽视”的物理劳动,我们害怕自己从“分析师”和“程序员”变成“建筑工人”和“厨师”。
这本身,就是一种不把大多数人当人看的视角。
所以,这种“下沉”的恐惧——这种“我不想去当建筑工人”的焦虑——它真正应该驱动的,或许并不是让我们去疯狂内卷地学 AI,去抢夺那 40% 内部越来越少的“数字”岗位。
它反而应该让我们第一次真正地去直视那 60% 的现实。它应该驱动我们去思考:为什么“物理劳动”的环境和待遇如此之差,以至于我们将其视为“末日”?
这种恐惧,恰恰是改善那 3 亿或 21 亿人劳动条件的最好动力。
说得再刻薄一点,也许 AI 最大的功德,还真就是把所有人都从“脑力劳动”的幻觉中扫地出门,让所有人都“下沉”到“物理劳动”领域。
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,“改善劳动条件”才会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
毕竟,当所有人都成了建筑工人的时候,那些曾经的优绩主义者再也没法用“我坐办公室是因为我当年努力学习了”这种扯淡的理由,来对他人的高温补贴和工伤保险视而不见。
所以,当我们谈论“AI 改变工作”时,我们或许都搞错了一件事。AI 带来的,可能根本不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“智能革命”,它更像是一场针对那 40%“数字劳动力”的“内部洗牌”和“阶层恐慌”。
它改变不了那 3 亿中国劳动者的物理现实,也改变不了那 21 亿全球劳动者的物理现实。
这么看,AI 确实可能改变(我们的)工作,但要说改变(所有人的)工作,那还差得远。
下次再有“数字精英”跟你贩卖 AI 焦虑,让你赶紧“拥抱变化”,迅速买课。
你大可以点点头,然后反问他:“那你……报新东方的厨师班了吗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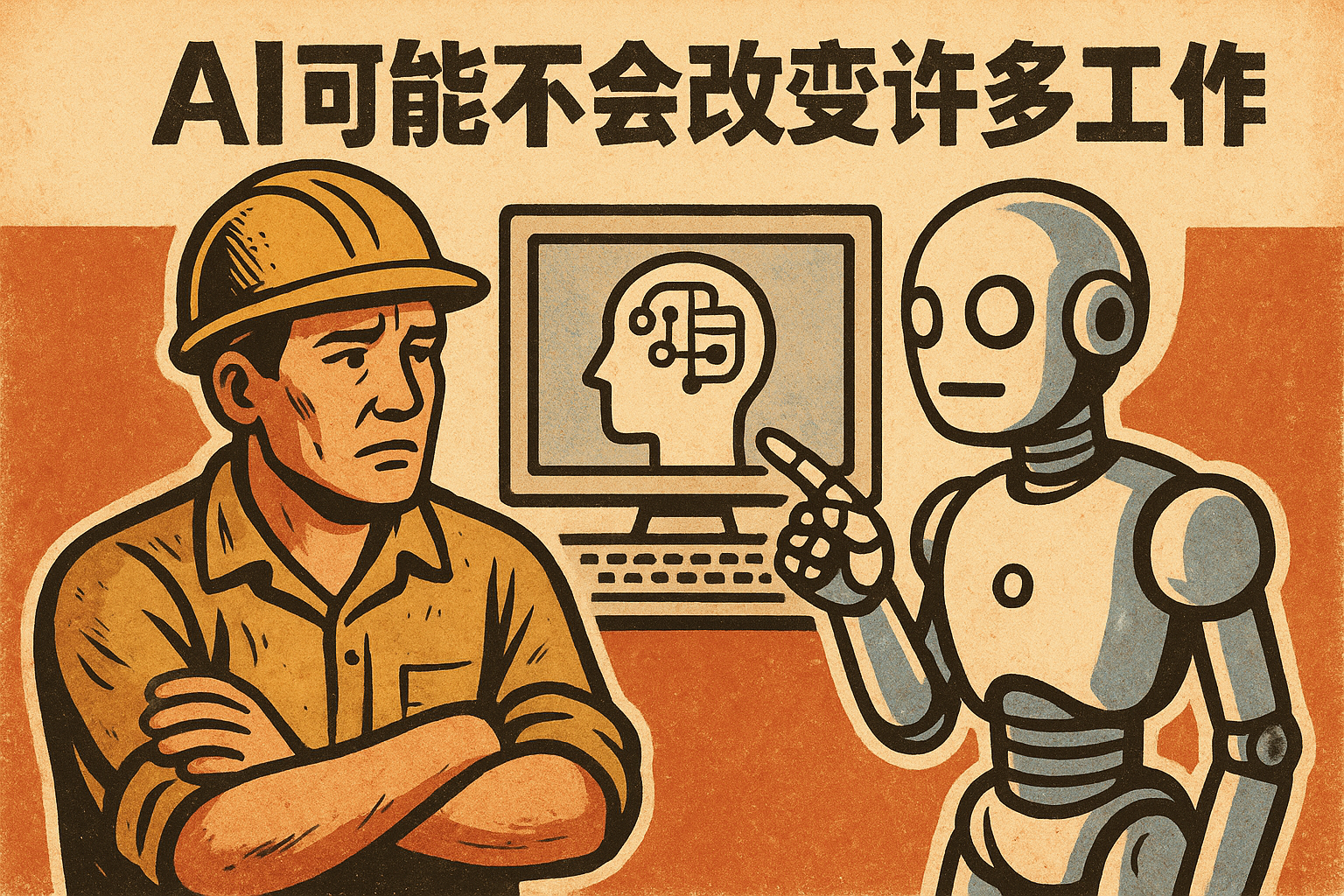



精选评论
AI可以替代某个具体的工作,但无法替代某个具体的岗位
您忽略了远程临在这个解决方案。
远程临在会是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期,我判断是如果远程遥控能远程刷马桶清洁浴室了,那大概不到两年,远端的操作者也就不需要了。
现在还有一个观点,就是责任ai如何负责的问题。
反脆弱!
说来好笑,很多工作之所以存在,不是因为科技不够发达,而是没什么赚头(ROI低)。直到未来有一天,科技在解决其他某个高ROI的问题时,不经意间一侧身,顺手就摧毁了一个老行业。
前提是,被赶到“物理世界”的前“数字劳动力”还有权力发声反抗,不然结局就是那种中产阶级被彻底消灭,只有资本和”蝼蚁”的赛博朋克反乌托邦。